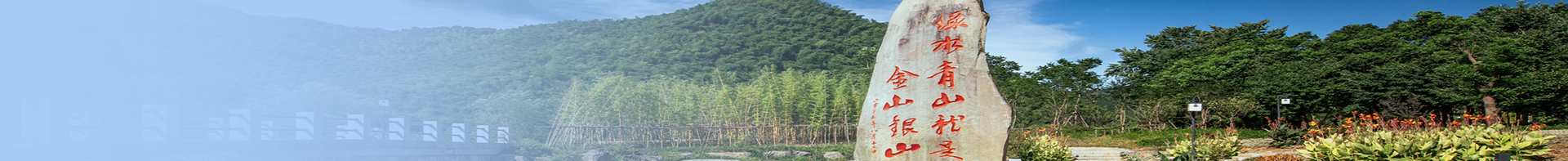申萬宏源報告指出,2014年下半年以來煤炭脫困會議級別之高、政策出臺頻率之密集均超市場預(yù) 期,但最終收效不佳。這些政策主要集中于遏制煤炭行業(yè)超產(chǎn)和給煤炭企業(yè)減負兩方面,雖然一定程度上有效緩解了煤炭企業(yè)經(jīng)營壓力,但產(chǎn)能過剩問題未獲有效解 決,而且,減負措施降低了行業(yè)邊際成本,使價格進一步下跌。
“2014年密集出臺的煤炭脫困措施沒有顯現(xiàn)成效,主要原因是沒有抓住去除煤炭產(chǎn)能這個根本問 題。不過,最近有關(guān)煤炭業(yè)的政策已從為企業(yè)減負向去產(chǎn)能靠攏了。”煤炭行業(yè)分析師劉冬娜說,“煤炭業(yè)去產(chǎn)能是指一些成本高、綜合實力弱、 煤質(zhì)差,虧損嚴重的企業(yè)永久退出市場,或一些煤質(zhì)好但規(guī)模較小的企業(yè)進行資產(chǎn)重組。但目前來看,上述兩種去產(chǎn)能情況還未真正出現(xiàn)。”
國泰君安報告指出,本輪煤炭行業(yè)去產(chǎn)能發(fā)生在我國經(jīng)濟增速換擋和結(jié)構(gòu)調(diào)整的轉(zhuǎn)折期,潛在的經(jīng)濟增長率低于上世紀90年代產(chǎn)能過剩時期,并且需求端改革空間已十分有限。“如果去產(chǎn)能力度與上一輪相當,將使得短期內(nèi)經(jīng)濟增長過度承壓。因此,本輪去產(chǎn)能的力度和進度將弱于上一輪。”
上一輪去產(chǎn)能時的過剩產(chǎn)能主要集中于以紡織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(yè),而本輪則集中在以鋼鐵、煤炭等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(yè),成本構(gòu)成中固定成本比重大,經(jīng)營杠桿系數(shù)高,直接的行政手段強制減產(chǎn)甚至停產(chǎn)的成本更高,阻礙更大,見效也相對緩慢。
事實上,國務(wù)院2月5日發(fā)布的《關(guān)于煤炭行業(yè)化解過剩產(chǎn)能實現(xiàn)脫困發(fā)展的意見》,已經(jīng)明確了煤炭去產(chǎn)能的政策著力點和進度,即要求煤炭行業(yè)在近年淘汰落后產(chǎn)能基礎(chǔ)上,用3至5年時間再退出產(chǎn)能5億噸左右,較大幅度壓縮煤炭產(chǎn)能,適度減少煤礦數(shù)量。
目前,山東、山西兩地已對上述《意見》做出回應(yīng),但其他地區(qū)還未有相關(guān)反饋,去產(chǎn)能如何落實、 人員如何安置、資金如何扶持,重組以誰為主體等尚無相關(guān)政策細則。廈門大學(xué)中國能源經(jīng)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指出,煤炭業(yè)去產(chǎn)能的過程復(fù)雜而漫長,也正因為 如此,保持當前政策方向的持續(xù)性將十分關(guān)鍵。從這個角度來講,2016年正在成為中國煤炭業(yè)去產(chǎn)能的一個“大年”。
2015年后政策轉(zhuǎn)向為去產(chǎn)能,將真正使得行業(yè)從供給過剩向去產(chǎn)能轉(zhuǎn)變。特別是地方政府此前基于稅收和就業(yè)兩方面的思維定式已有所松動:煤炭行業(yè)虧損嚴重令很多省份從煤炭企業(yè)所獲得的稅收遠少于提供的補貼,加上中央財政安排資金合理解決人員就業(yè),地方政府兩大顧慮消除,去產(chǎn)能積極性極強。